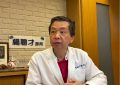【记者/赵宥宁 摄影/甘岱民】
在许多类型的表演或宣传中,常会看见与原住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内容成果。但当主事者对原住民族文化并非足够理解,文化错置、牛头不对马嘴的无理局面也就经常发生。
就在半年前,政治大学校运啦啦队竞赛曾有系所以“海洋奇缘”为主题,穿戴有原住民族意象的服装,但表演内容却充斥对原住民文化的刻板印象,以及错误拼凑的文化再现,事后引来了各界批评。
近期由政大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在政大校内举行了“‘看见’原民周”系列活动,12月13日和政大搭芦湾社举办“族服的想像、想像的族服”讲座,邀集原住民社员分享族服与自身生命故事的连结,希望让更多人理解族服背后代表的文化意涵,看见真正的不友善,未来才有更多发展的可能。
冯晨峻,Parece Darularumun,鲁凯族

来自屏东三地门乡德文部落的鲁凯族青年Parece darudarumun说,从他出生以来,每个人都会有一套奶奶或是外婆制作的族服,随着年纪的增长,也会有各套不同款式的族服。
却因为太习惯在家乡穿着族服这件事,让Parece darudarumun曾一度以为每个原住民族人应该都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族服,直到上了大学后,认识了更多原住民朋友,才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能有都套自己的族服,这才促使他回头思考族服的意义。
谈及族服对他而言的重要性,Parece darudarumun表示,族服除了是用来识别身分的一种方式外,“珍视族服更是珍视家人对我的爱,也是珍视我所拥有的文化”而他也支持那些正在找寻自己族服,努力追求文化、身份认同的人。
黄昱,Piling suyan,泰雅族X布农族

回想小时候穿着外头租来的族服站上市府颁奖台的自己,Piling suyan说“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族服”,却不知族服从哪里来,也不知道族服代表的意义,Piling suyan更开始疑惑著“为什么我没有自己的族服?”
带着疑惑奔向父母,才明白原来族服早在父母那代就断了传承,目前部落保有的族服,都是外婆那辈留下来的。而他所处的新佳阳部落,族服更是别于一般泰雅族的红色,改以紫色来妆点,当Piling suyan追问长辈后才知道早期新佳阳部落迁移时,在定居地找不到红色的染料,就以紫色来代替。
虽然族服的传承在父母那代有了断层,当时高中毕业将升大学的Piling suyan仍向往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族服,布农族的母亲甚至为了儿子的愿望,去学习织布技术,但族服对Piling suyan来说,有着必须沿袭的传统。
因此他认为“不管什么情形,我一定要了解我身上的族服代表的意义为何。若对自己的族服和族群一无所知,如果随便穿,就不会像是族服,乱传的族服没有文化的重量。”因此,穿上属于自己的族服这件事,对现在的Piling suyan来说,还有段路要走,他觉得自己还没资格拥有族服。
林诗函,Siko Paylang,阿美族

从小在台北长大的阿美族青年Siko Paylang,每逢丰年祭就会跟着父亲回到台东都历部落共襄盛举。至于族服对Siko Paylang的意义,在她成年之前,她一直都认为“族服就是一件会在丰年祭时穿的衣服”,也是套看起来跟其他衣服不一样的衣服。
直到成年后,父亲问Siko Paylang要不要跟同阶级(年龄相仿)的人一起参加丰年祭,这话一出,让过去总是参与父亲阶级丰年祭的Siko Paylang意识到,原来她对自己的阶级根本一无所知。
所幸后来有堂弟带着她进到Pakalongay(最小的)阶级,陪Siko Paylang走访了一段寻根之旅,从头学习自己的文化。Siko Paylang也分享,当部落里每个青年成年时,男生会由他女性的长辈为他穿上族服,就在堂弟成年的那次祭典,堂弟问“姐,你可以帮我穿族服吗?”让Siko Paylang觉得穿族服是件特别的事,除了穿得漂亮外,穿上的更是责任感,代表要开始带领弟弟妹妹们成长。
从小在北部长大的Siko Paylang,虽然有自己的族服,也对自己的文化有了认识,却还是常质疑“我到底是回到部落的台北人,还是住在台北的部落年轻人?”,也常面临到自己内心的身分碰撞,但话锋一转,谈到族服的意义,Siko Paylang仍坚定地说,是部落给自己的身分证明,也代表着某种身分象征。
你知道族服的文化意义吗?
回到问题的根源,为何那些表演者会想穿上原住民族服来再现他们眼里的“原住民文化”?现场有学生认为,无疑是表演者为了要满足场域里人们的欲望,展现一个特别的东西,求一个片刻的高潮。然而,那场表演的初衷,并非源自于表演者想要展现自己的主体性,而是当能满足观众猎奇的欲望之后,在那个政治场域里,表演者也许可以拥有一个更好的阶级。